张大千与榆中兴隆山
2025年02月28日
字数:3,685
版次:03
高 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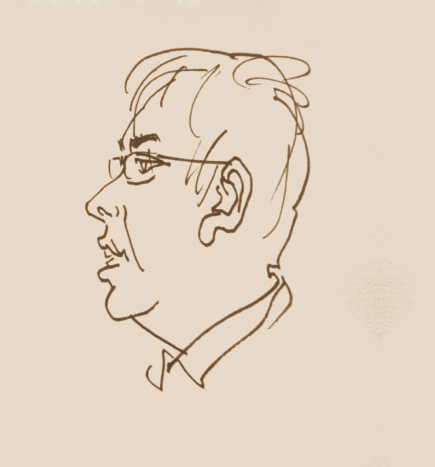
高羔 甘肃兰州人。长于黄河岸边,酷爱文学与历史,常问学于地方史学家张令瑄先生,曾与董鼎山、陈忠实等文坛大家鸿雁往还。先后参与了《走近兰州》《七里河区志》等书籍的编纂。
1941年春,张大千偕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一行三人,以及500公斤行李,由成都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抵达兰州。
杨宛君为张大千的三夫人,原名杨梦兰,为北平唱京韵大鼓的艺人。据后来任张大千中、英文秘书的冯幼衡在《形象之外》一书中称:“梦兰(杨宛君)有燕赵儿女豪气,又时作男儿装束。”张大千之所以在他的几个夫人中带杨宛君去敦煌,也许正是因为杨宛君的豪侠之气,或能吃苦这一点。
当张大千一行所乘的飞机在兰州的东岗机场落地后,时年42岁的张大千走出机舱,有人曾这样描述初到兰州的他:“中等个头,连鬓的花白胡须有一寸多长,二目炯炯有神。身着一条灰色对襟的四川大褂。他和蔼可亲,言谈风趣。”
可是,就目前研究张大千的一些文字资料来看,张大千究竟何时到达兰州,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民国时期曾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金石学家、学者张鸿汀先生之子,甘肃文史馆馆员张令瑄曾口述,由唐国华整理的《陇蜀千里翰墨缘》记载:“1942年,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从四川经陇南、天水等地,来到兰州。”
另外,左彦福在《张大千先生画兴隆山》中写道:“1938年,张大千先生前往敦煌考察,途经兰州时,下榻于七里河的吴家园。”
白巍在《画坛巨匠——张大千》一书中写道:“1941年5月初,张大千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心智再赴敦煌。他们一行三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
李永翘在《张大千年谱》中写道:“(1941年)5月初,(张大千)先生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再赴敦煌。从成都动身,先坐小飞机抵兰州。”看着这些张大千到达兰州的时间,有的甚至相差两、三年,真令人感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时跟随张大千一同前往敦煌的、大千先生的次子张心智在《张大千敦煌行》中写道:“1941年春末,父亲带着姨母杨宛君和我共三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
似乎,就连张大千自己也因年高事远而记忆模糊,他在《我与敦煌壁画——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专题讲演词》中说:“我到敦煌,是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间,带同家人前往。”
这给出的众多时间,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这似乎成为一个悬而未决之谜。
只有戚宜君在《张大千外传》中好像给出了具体的日期:“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八日,张大千带着三夫人杨宛君及次子心智,以及一应用具和行李五百公斤,舍弃了陆路的跋涉,由成都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直飞兰州。”那么戚宜君说的对吗?张大千是在“三月八日”到的兰州吗?
笔者后来看到《收藏家》杂志刊发了一篇《上海成都民间收藏张大千书信选注》的文章中,有一封张大千致张目寒、谢稚柳的信函。
目寒、稚柳两弟左右:四月八号来兰州,以交通困难,迄今尚未得出关也,奈何奈何。此间搭车之难,远过四川。坐货车其危险之大,不堪设想,即不危险,其风沙亦非我辈所能禁受,况货车亦坐不到。此际正在托人看是如何耳。此一月来曾赴榆中元凤处,游兴龙山、谒成陵,又往青海,观光塔儿(尔)寺,差为满意,余无善可告。元凤近来兰州,王艺圃昨日亦到,今日有电话来,云明晨来访,见时看伊有无方法觅西去之车也,恐亦不易。风闻重庆日前被炸,确否?极念,望两弟复书告之。佩苍兄枉贺太和场,而天风海水图乃藏于犀浦友人家,弟行前匆促,未能往取,致令虚行,罪甚罪甚!乞转告之。俟弟归时寄上,绝无贻误也。爰再拜。五月八号艺圃来访,知上清寺被炸,弟受惊否?兄定星一西上。
张目寒和谢稚柳是张大千的好友,从这封信我们总算知道了张大千是“四月八号来兰州”的确切时间,也就是说张大千是1941年4月8日到达兰州的。并向张目寒、谢稚柳叙述了来兰州一个月内他先后去了兰州以东的榆中县游览了兴隆山,拜谒了成吉思汗陵,又前往青海西宁塔尔寺观光。可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西行的车辆很少,所以正为寻觅西赴敦煌的车辆而煞费苦心。
张大千信中所提到的“榆中元凤处”,是指时任榆中县县长的马元凤。马元凤为陇西县文峰镇人,曾任《安徽日报》主编。另外王艺圃,原名王漱芳,字艺圃,贵州盘州市人,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兼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董事长。张大千把西行找车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张大千一行在游览兴隆山时,正值春季,也是兰州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春光明媚中,兴隆山显得更加郁郁葱葱。张大千在马元凤和弟子刘君礼等的陪同下来到兴隆山脚下。因山形似龙腾,在清康熙年间取“龙兴云而云从龙”之意,故又称为“兴龙山”。
张大千一行一路兴致勃勃地观赏奇松山色,还拜谒了刚暂厝于兴隆山大佛殿两年的成吉思汗灵榇。
张大千游览兴隆山时,感到西北荒芜干旱,但这里却有茂林清泉,颇有南方的景致,这更激发了他游览的兴趣。
他们一路兴致勃勃地来到兴隆山之腰处的太白泉。太白泉为一座两层小楼,掩映在婆娑的枝叶中。一楼正殿塑有麒麟送子,四壁则绘有一百个神态各异、天真活泼的童子。就在正殿的供桌前,有三个泉眼,泉水清澈甘冽,当地百姓称之为“圣水”,传说可治百病。二楼塑有太白金星神像,据说很久以前,兴隆山一带遭逢天灾,大旱不雨,天上的神仙太白金星闻知后,为民布雨祈福,并点化此泉,故名太白泉。当地的善男信女又多在泉中摸索,传说若摸着石子则生男孩、摸到瓦砾则生女孩,故又称之为“摸子泉”。登临二楼,凭栏远眺,远可望马衔山终年不化的积雪,近可见兴隆西山栖云峰郁郁葱葱的山色和点缀其中的楼台亭阁,真可谓远山近景皆在眼前,令人心旷神怡。
山上的道士见一位长髯长衫的大师远道而来,又有“县太爷”陪同,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道士们用清冽的泉水沏了茶,张大千品呷了一口,连连称赞泉甘茶香,真好喝!他与马元凤及刘君礼一边饮茶一边与道人们聊天,询问兴隆山一带的风景、物产和风俗。
当晚,张大千一行夜宿于太白泉,张大千还连夜根据白天游览时所见所感,绘成《兴龙山图》一幅,并题跋:“辛巳三月同元凤、君礼游兴龙山,谒成陵,夜宿太白泉。明日还兰州,写东山玉皇观,用二石法,似一涵仁兄法家博教。大千弟张爰。”另钤“张爰、大千居士”两印。其中“一涵仁兄”为时任甘宁青监察使的安徽六安人高一涵(1885—1968)。因为据张心智在《张大千敦煌行》中回忆:“在兰州期间,我们分别住宿在高一涵和鲁大昌两位先生家里。”也许是为了感谢高一涵的接待,张大千特绘了这幅《兴龙山图》赠予高。
第二天一早,张大千一行从东山下来,又登上西山“栖云山”。在山巅之上,大千先生俯瞰远方,在阳光的照耀下,兴隆山林木葱翠,庙宇楼阁点缀其间,远处的山顶尚有未融化的积雪。这使大千先生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峨眉山顶也有季节性的积雪。在兴隆、栖云两山之间有大峡河潺潺流过,云龙桥横跨其上,景色真是美极了。作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一代画师,在将这些美景录入眼睛的同时,更要映在心里,出于笔端。他拿出画板,细心勾勒着兴隆山的轮廓,把眼前的美景绘成一幅草图。在结束绘事时,他一边收起画板一边说:“再过几天,等到野花开了,这里一定更美!”后来,他在草图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创作,绘成《兴龙山色》图,并题跋:“榆中兴龙山,林木蓊郁,居然南中景色。予以春暮来游,高处犹雪,则与吾蜀峨眉同也。辛巳三月。大千居士爰写于皋兰客次。”钤“张爰之印”“大千”两印。《兴龙山色》在2010年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出170万元港币高价。
此外,张大千还画有一幅《山中幽居图》,但这却是在张大千游览兴隆山五年后所作,也许正是根据当时的写生草图,加上回忆与构思,创作出了这幅图,而这幅图也是其兴隆山系列题材中,较为写实的一幅。画面下部从横跨大峡河上的云龙卧桥开始,穿过云龙卧桥沿山径蜿蜒而上,依次为山神洞、青龙盘石、大佛殿、太白泉等景观,这些兴隆山标志性的景点皆收录于画面。
《山中幽居图》尺幅为112.3cm×46cm,画面意境高远,构图严谨巧妙,落笔疏密有致,色彩上多以浓淡墨为主,个别地方略加赭石点缀,如树干、屋宇等。最上以淡墨染出远处的终年积雪的马啣山,给人以旷远辽阔之感,使人产生无限遐想,足见大千先生对景物细致的观察及精深的艺术造诣。
最后大千先生在画面的上部题有一段长跋:“癸未初夏,颂言仁兄相晤安西,时予有榆林窟之行,信宿即别。同年十月,予在皋兰七里河嵩龄别墅,先生伉俪远道见过,又以还蜀。仆夫以戒,行李在途,不复得写数笔,将意倾去,穷虏催伏。先生于役山海关外,为国家多故,停辙故都,予时北来,握手为欢,漫为写此。此榆中兴龙山,先生旧所游履,王禹偁之未见明年又在何处,能无慨然耶?丙戌开岁,大千张爰并记。”钤白文“张爰之印”和朱文“大千”两印。这幅画现被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张大千在题跋中所说:“王禹偁之未见明年又在何处。”这里面还有个典故,王禹偁(954—1001)是北宋诗人、散文家,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故屡遭贬谪。他所撰《黄冈竹楼记》中有“未知明年又在何处”,这是因为他频遭贬谪,奔波不息。而张大千似也有同感,故发出了不知明年又在何处的感叹。
一幅画讲述了一段历史,张大千在时局维艰的情况下,不畏困苦,深入荒滩戈壁临摹壁画。同时,更可透过这幅画作,看到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全民奋起抵抗外侮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七辑)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数字报首页
数字报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