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故乡的柔情
2022年07月18日
字数:3,000
版次:04
牛旭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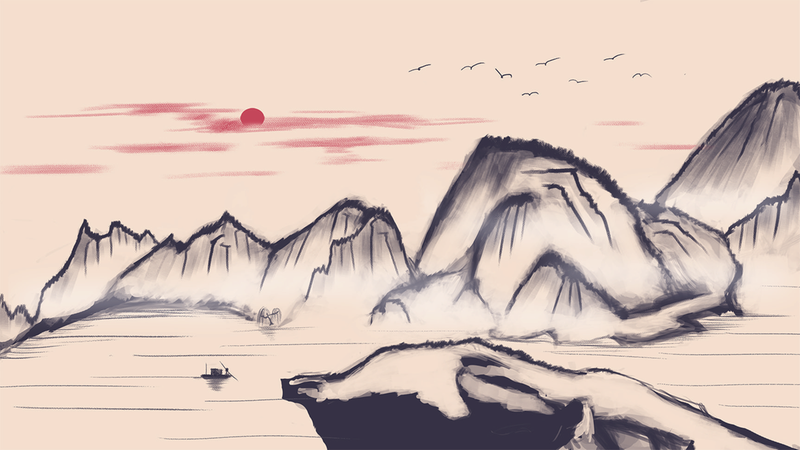
疫情胶着的紧张时期,收到了军平先生从上海寄来的新书。他抱歉说由于物流防疫管控,书没有签名。
似乎注定要留下遗憾。就像他极力书写的,绝不止乡愁。
大千世界,皆在网上。他是我在网上认识的,追故乡的朋友之一。同样,这本书也写给他的故乡甘谷和他的父亲,写他父亲的村庄。
让人难过的是,他的慈父已经不幸去世,文中更多的,是他无法弥补的抱憾,而带来积缠着他的愧疚。
西北的角落,绵延的黄土地,还带着苍黄的本色。种庄稼的人,都还弓弯着压趴的腰。这也只是岁月的平常。读他的书,便走进他的童年,而给我生命的感同身受:人的苦,只有经历过苦的人,才知道,才配理解。
书中满纸都是的怀旧,证明他还单纯如往。
白配灰的远山眺望,是他新书《父亲的酸刺湾》的封面。清风扑面的质朴之气,让我喜悦于走向世界的人,没有被花花世界酱染。
这些年,他还试图以文字的怀念,在上海,而重返过去,或者找回所有的流逝。恰如我,没心没肺没出息地追故乡。
同命相怜里,我从接先人、祭山这些乡村独有的古老民俗里,体察世事人心的尺度与规程,看到他散文的亮点。又从夏收、秋种这些寻常的农事里,感恩农业的哺育与滋养,这是他作别故乡的反刍。他一直在追寻……
但能找回来的,只剩记忆。
如同春节团圆回到的乡村里,在那短短数天,游子会听到吹过一世的风声,也会在年关和清明这样的时节,抑制不住地想念亲人,追忆父亲,以及生活的悲欢离合,岁月的五味杂陈,劈头盖脸的白雨,忽闻下彻的大雪。最后的最后,眼望着、撒开手与父亲的别离画面,字里行间浸满命运的无奈,浸透为儿负罪的谦疚,写出了平平凡凡的父子情,说出了一个酸刺湾庄稼汉艰辛的奋斗,和努力对抗坚硬的现实,而用佝腰茧手做出的一丝改变,何其不易!何其伟大!
军平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散文和诗歌,看似零碎,但语言朴实、凝炼,情感真挚、动人,故事细腻、温情,用不紧不慢的叙述,记录一个离乡者,背负故乡与亲人后,心头解不开的孤独与枷锁。现实庞大得令人茫然,社会变幻的没有停歇。在对时间的认知里,他深知“此期再无期”,在对空间的回归里,他又皈依奉养他并已收留了父亲的吾乡吾土,是他灵魂永将摆渡又将一生放不下的酸刺湾、芦子崖湾。
最后的时间,一个人的车站,归宿,在貌似借着诗歌的轻松明快里,却已感觉到生命驿站里叫家的那个落脚处,愈来愈模糊。也许只有半路失去亲人的人,才懂得这种暗含着肝肠寸断的悲凉与伤感。
不禁让人唏嘘,我们都是这世间的过客,来了终要去,在血缘与宗祖的亲情维系里,我们能活得更好,或者能努力活成更好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这是他的父亲所理解的生活,逃离的孩子是为了生存。
作为他的甘肃老乡,我知道他所写的最后的天水市第一医院,是具体而又真实的存在。院门口,也是有家的人,一定魂牵梦绕的地方。他那天晚上连夜赶回家的路上,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路。那不止三遍的“快到了么”的追问,一次次在分割他与父亲的距离,他离得越近时,父亲走得越远。
他将重病的父亲按风俗送回庄宅时,他不知自己是罪恶,还是孝顺?其实结果从很早就开始了,那是一个农民种地、收割,农闲当麦客,拼尽全力盖房子,打工当泥水匠,风湿,结核病,会有的料想中的结局。劳动者有创造的辉煌,必然也有自殒的悲剧。军平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打小看到父亲的艰辛,却没有闲暇,在有能力的时候陪伴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挖着他的心。
几年后,千里外,他成了个从谷歌地图上,反复搜寻和追祭安埋父亲那片坟地的儿子。
苏童说“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的居住地,他便会在一草一木之间看见他的幸福。多少人现在生活在别处,在一个远离他生命起源的地方生活着。”军平的父亲一辈子属于村庄。他的经历正是如此,而才有了带着痛苦与磨难的文字,尽管克制,却另有深义。
文字是戳心的,回答了我们人生的许多面对,也源于他非虚构的自我解剖。流浪远方的人,常常辜负故乡,又错认他乡。甚至不想承认,我们终要与故乡与山河与亲人和故人最终作别。童年,只是刻在一个人命里的一截时光,他多次写到母亲、家人和族亲,写到乡俗、规程和忌讳,写到黑暗中天边的光亮,渗透着浓郁的烟火气、沧桑的岁月感。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出走者,但他不是背叛者,而必然是一个回归者。在故乡人事的生老病死与万物的除旧布新里,他有他对酸刺湾,毫无功利之心的无上敬重。他像小时候被弹到找不见影的弹珠,又像被一条皮鞭抽打飞旋而起的陀螺,时时回望着起步的地方,对着母亲的怀抱倾诉,对着大山大坡倾诉,一个永世长不大孩子的忧伤。
还会哭泣,还会缄言。这种本能让他抛开私心杂念,把美好写进书里,让生活的涓滴干净如水,让现实的块垒卷舒如云。曲曲折折的命运,是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让他彳亍其上,并不一定撑起,横跨久违时空的船。
周国平说:“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对于酸刺湾的父亲,他是好运的,对于上海的异乡人,他又是孤苦的。每每读完他的一段追忆,都会有一种锥子在剜的痛彻心肺,还会有令人难忘的时光欢快,主要是那种镌刻在童年,抹不去又洗不掉,而镶嵌在心田的日常美好与清贫寡淡,会令人沉默许久、沉思良久。令人再次想起崔京浩演唱的歌曲《父亲》,这首老歌,是电视剧《咱爸咱妈》的主题曲,它让我一听到“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的旋律,就忍不住泪眼朦胧,往事依依。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好父亲,但当我们翅膀硬朗、远走高飞后,我们深陷入自以为繁忙又不可摆脱的新世界,遗忘了父亲很远,忽略了父亲很久。与父亲的时光,似乎从学步,一下子走到了送别。
当下,迅疾里要顾全生活的价值,只有在取舍中,变得无情而冷漠。人不是想不怎么样,就会不怎么样的。我们能够掌握的毕竟有限,能够顾及的,会越来越少。
没有挽留住的,是曾经用生命护佑我们的亲人。他与中国的所有父亲一样,为了儿女和儿女的幸福,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盖房子,舍不得治病,但他却舍得汗水,舍得尊严,舍得体力,即使在他步入晚年之后,他依然以一个农民,在世场不停的扰攘,在名不见经传的一屲湾地里,与风雨为伍,在劳动中缓缓躬腰、慢慢消瘦、渐渐骨缩,甚至从不对儿女说一句艰难,常年还在外风餐露宿,打工挣钱。同样,也是拼死拼活与旱渴的对抗,让他成为村庄里,改写家史最有尊严的人。
有尊严的人,相反会活得卑微。这也是他的处世,是他作品的基调和反复出现的词语。
他在后记里这样写到:“先父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是一个资源匮乏的饥馑年代,和大多数在这个干山枯岭上务农的同辈人一样,历尽艰辛世事,常年劳作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以维持薄弱的家庭,供养子女,日复一日,如一粒尘埃,用谦卑和敬畏奔波在岁月的时空里……”
读到此处,我不禁心里一疼。他所叙述的生活,其实是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众生之路,他所追念的酸刺湾,其实是每一个离乡人的故乡,他所亏欠并将终生为此负罪的父亲,是多少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间蹉跎!
我们忘记父亲的,岁月不会原谅。故乡容不下父亲的,时间一天天会树起丰碑。
渭河北岸,水逝云待。酸刺湾,是走出黄土地的人儿,交上心头的万念情深,是世间路道的坎坷与深谷。她不论有多小,军平一辈子都无法走出。哪怕他在都市上海,能够慰藉他的,是这小小的村寨。
天生所给他,赐予他与生俱来的本真,如他父亲,从不苛求于世的本本分分。
那地方草长得茂盛,房子很旧,那时候黄土满山,时光很慢,父亲肩上坐着儿子,儿子跟随父亲身后,每一寸土地和光阴,都那么温暖迷人。

 网站首页
网站首页 数字报首页
数字报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上一篇
上一篇